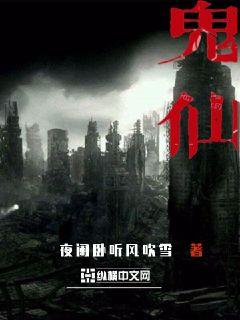
鬼仙能活多久
本書作者:夜闌臥聽風吹雪動 作:連載,直達底部
最后更新:2021-11-30 10:30:08最新章節:第二百六十六章:拜會楚老,受益匪淺!
魑魅搖扇,魍魎端茶。孟婆拄杖侍奉左右。閻王爺更是滿臉殷勤地為其捏著肩膀。顧墨單腳踩在閻羅書案手里拿著一把的好牌,黑白無常臉上貼滿了白條。牌局作罷,顧墨癱坐在陰司第一把交椅上平淡如水地說:“永生真的有意思么?”頓時鬼差陰兵全都啞口無言,閻王爺輕咳一聲小心試探。“司命大人何出此言呢?!”顧墨仰頭嘆息,黯然神傷……人人覬覦的永生卻被一個小小的香燭鋪老板做到了,然而獲得永生的機緣還得從一場驚魂夜說起……
推薦閱讀:
皇叔借點功德,王妃把符畫猛了
釣系玫瑰
開局,我把仙人算死了
開局,我把仙人算死了
躺平:老婆修煉我變強
封總,太太想跟你離婚很久了
權力巔峰
諜戰:我當惡霸能爆獎勵!
你的機緣很好,我笑納了
出家為尼后,哥哥們跪求我還俗
鬼仙是什么仙
鬼仙都有哪些仙家
鬼仙莫衣
鬼仙一般找什么人上身
鬼仙之祖
鬼仙和鬼的區別
鬼仙附體的癥狀
鬼仙大人呆萌吃貨懷里來
鬼仙人
鬼仙是好的還是壞的
鬼仙兒的小說
鬼仙需要修煉多少年
鬼仙人仙地仙天仙神仙
鬼仙悲王上身的具體表現
鬼仙堂弟子出馬前癥狀
鬼仙派
鬼仙為什么會到我身上
鬼仙投胎轉世是為什么
鬼仙洞酒
鬼仙上身的感覺與癥狀
鬼仙和地仙的區別
鬼仙悲王是什么意思
狐仙一般找什么人上身
鬼仙清風
鬼針草有什么功效
鬼仙溝 電影
鬼仙怎么供奉
鬼仙小說
鬼仙打竅的癥狀
鬼仙溝
鬼仙地仙人仙天仙
鬼仙子穿越小說
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的區別
鬼仙堂弟子壞處
鬼仙之祖是誰
鬼仙有哪些
鬼仙和清風仙有什么區別
鬼仙朱砂
鬼仙有什么能力
鬼仙女神
鬼仙瓔珞坐標
鬼仙之才
鬼仙再修煉會成什么
鬼仙藍眼黑曜石
鬼仙堂口堂單怎么寫
鬼仙派宗主實力
鬼仙紅眼黑曜石
鬼仙轉世的人會怎樣
鬼仙石
鬼仙石三根
鬼仙能活多久
鬼仙能送走嗎
鬼仙石電影
鬼仙石在線觀看
鬼仙怎么送走
鬼仙石是什么東西
鬼仙可以修成天仙嗎
鬼仙和地仙誰厲害
鬼仙厲害嗎
鬼仙掌堂教主
鬼仙上身有什么什感覺
鬼仙悲王主要管什么
鬼仙都有誰
鬼仙奇緣